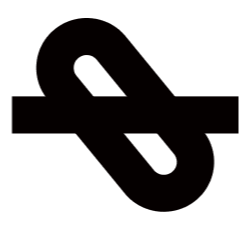王子耕:我和父亲在1994年
我父亲是一个基本不表达自己的人。在他那里,西方那些你爱我、我爱你什么的,绝对不会出现。这也是挺典型的中国式父子关系。 在一个单亲家庭,或者再婚家庭里,作为之前的孩子,会比较没有安全感。但是你从很多的侧面,又会发现,其实他是爱你的。他是在乎你的。 我想记录这个,或者说,以这作为一次告别。

这个装置缘起于小时候我和我父亲共同度过的一段时光。 1994年,我的父母离异,我父亲租下北大燕东园的一个院子当作办公室,制作树脂工艺品,我跟着他在这里暂住。两年后他结束这段短暂的创业重新回到体制内,我也小学毕业离开这里。这是我唯一和父亲单独相处的两年。 为了方便我上学,我的父亲在他办公室的货架后搭了一个单人床,这里便成为我临时的家。我坐在床上,透过货架观察父亲办公室的记忆成为了这个作品的起始点。两个联动的单人剧场交互开合,通过窗口,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虚像置身在1994年的父与子不同的梦境里,也可以在某一个刹那与对面的陌生人不期而遇,彼此的像出现在同一个空间内,却无法交流。或许你也和我一样,期待一个熟悉的而又不可能出现的背影。这件作品起始于我个人的父子回忆,同时也是亲缘关系中的依赖、对立、和解和遗憾的轮回。 2020年冬,我的父亲病故。我在父亲的病床前接到一个装置的委托,并将它命名为1994年。 ——王子耕作品《1994年》介绍 于崔灿灿策展《做更好的人——新一代的工作方法》 北京 山中天艺术中心 正在展出 (详见文末)

1994年 王子耕 根据全球知识雷锋音频采访整理

这个作品的起源,其实是去年的时候梁琛在上海OCAT策划了一个展览,他当时邀请了几个年轻的建筑师,来讲他们儿童时期对某一个空间经验的理解。 梁琛给我打这个电话的时候,我在北京东肿瘤医院,我爸的病床旁边。当时我爸已经是胰腺癌晚期了。 接到这个电话,我当时就想到了小院子。这个小院子,大概是94年到96年,我爸跟我单独生活的地方。当时我10岁,我爸跟我妈刚离婚,他就带着我在小院子住。 当时这个地方也不是一个住宅,他租下来是为了自己做个小作坊。所以,他就在货架后面搭了一个床,这个床供我上学的时候能方便住宿。因为我的小学离小院子特别近,走路大概5分钟到。 我们在这住了大概两年的时间,一直到我小学毕业。之后我就去爷爷奶奶家住了,他也把这个厂子给关了、变卖了。他可能也觉得下海创业这条路走不通,就重新回到了体制内工作。他的人生里,也有了这么一个短暂的创业历程。
当时在这里的生活,那还是有很多印象的。 比如说工人就在隔壁,他们是做这些树脂制品的。树脂有点像石膏,但比石膏硬,有点像现在手办的前身。得先做一个泥塑的原型,然后再用硅胶来做倒膜。硅胶是里面这一层,外面那一层是石膏。倒完膜,然后调好树脂的原液倒进去。抽真空定型之后,就会形成一个最原始的模具。再经过一系列的工序,包括打磨、上色等等,最后变成一个产品。大概是这么个样子。

我跟我爸的交流其实不多。 我并不觉得我生活在一个比较正常的家庭,我爸跟我的性格也很不一样。然后我们学的东西也不一样,他是学化学出身,我们家也没人搞过建筑。 所以我在做这个东西之前,我一直觉得它不应该是一个特别甜蜜的、对童年的回忆,因为这不是我的童年。我的童年其实伴随着很多矛盾、不理解等等……复杂的情感经历。 我小时候觉得他不太是模范家庭里那样称职的父亲。他在我学业事业上也没有给过任何帮助,不太像一般的中国家庭,毕业了还操持你很多其他的事情。他都没有。所以,所以对父亲的态度还是挺矛盾的。 但是后来,就长大了之后,还是会发生一定变化。就是你会慢慢觉得,不只会以父亲的标准去看待对方、或者以父子关系去要求对方,而是从看一个正常的普通人,一个也有自己难处的人的角度去看待对方。
所以在这个影像空间里面,其实是两个独立的单人剧场。然后它们相互交合,相互有一开一合,不是这边开就是那边关。然后把彼此的影像,投射到一个场景里面。这个场景是依据我小时候在住的房子里,对空间经验的理解。

有一个背靠背的场景,有一个面对面的场景。但都是虚像和实体空间的一个拟合。所以,这里人跟人之间无法交流,但是是在一起的。大概是这样一个身影重叠的场景。


这个装置最开始是一个场景记忆,在货架的后面是当时我睡觉的床。那时候,我每天起床,透过货架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。所以我想以儿童的视角,在货架后面,再一层层透过去。这是最开始的空间原型,然后逐步演变为一个机械互动的影像装置。



它提供了两个视角,一个是儿子的视角,一个是父亲的视角。父亲的视角那边是很多缓慢旋转的风机,以及一个办公桌。他可以看见自己的影子,同时把对面人的影子也投射过来。这是一个面对面的场景。儿子的视角就是坐在床上的。通过玻璃的折射,他能看到自己的像坐在空间里的床上。床对面是摆满东西的货架。
对面父亲的影像是通过一系列的光路和电子的控制,把它通过一个斜向玻璃再投射过去,是一个背对背的场景。两边的场景一近一远,然后有一面是用平行镜面来延伸风机的,有一面是没有延伸的,所以它的空间感受也不太一样。这是一些设计上的细节。

我们都是通过摇杆来控制对面的光源。我们所有的主光源是一个逆光光源,然后通过控制光源移动来模拟阳光。透过间隙打下来的那种光感。同时当主光源移动到一定位置的时候,会触发一个传感器,然后会把对面的影像投射过来。

对面的影像也不是一直都会出现的。在你移动到某一个位置,它会像鬼魂一样突然浮现出来,又突然消失。刹那间会有一个跟对面的对话。

后来,因为这个装置在技术层面还有点复杂,我们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在光路上、在电子设备如何去实现它上的讨论跟设计。反复了很多次,有的朋友就建议,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拍摄一个你认为可行的背影。当观众摇的时候,就会出现拍摄的背影,而不是很复杂地去记录对面出现了什么。他觉得对面其实是不可控的,对面可能是男、女、老、少,都还是不可控的。 但是我后来就觉得,这作品的点就在于不可控。就像你不能选择你的家庭,你也不能选择对面的人是谁。你不知道对面是什么人,也可能是你的朋友,也可能是一个陌生人。

我想起一个我经历过的事情,2008年,我有一个要好的大学同学车祸去世了。有一天晚上,我们几个人,包括他原本已经快要结婚的女朋友,就坐在车上讨论他追悼会的事情。突然有一个人,从我们的车旁骑自行车过去。然后他女朋友就说,你们快看,那不是那谁吗?然后她甚至都下了车去看,看那个人是不是她刚刚去世的男友。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一种期待的。影像一闪而过、你认错人的时候,是一个很动人的瞬间。我想要表达这种层面。 这作品本身起始于我的个人记忆,但是它也并不是只停留在我自己的故事里。我觉得,人跟人之间、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的纠缠的关系、对望的关系、遗憾的关系。我希望能够是这样的一个装置。

我爸是去年12月去世的,他一直在住院。然后有一天突然通知,说已经不行了。我立刻从工作室开车到医院,到的时候医生说人已经走了,你晚了一分钟。 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一分钟之后,我才进的ICU。已经停了一分钟了。 我到他的面前,握住他的手,心脏监测仪又开始起跳。我赶紧叫医生,这明明人还没有过去。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已经无能为力了。 他的心又跳了差不多半分钟,又停止了。 你很难解释那个时候,给你的触动。
他在去世之前也没有见过这个作品,我也没有给他看过。 我只是说,爸,你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住在过院子里面? 他说,记得。 我说,我要做一个作品,可能是跟小院子相关的。 他说,好。 其他的,我也没跟他说过。